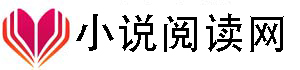220-230(50/70)
甚安!”皇帝病危昏迷的消息,连同割让荆北一地的旨意,同天到达,意外的,武大帅并未提要率兵入京请见陛下,兵逼太子行保皇之事,反而加快了对西炎城的收取脚步,或许在他心里,忠君与爱民的天秤已经倾斜,在保皇与保民之间,他选择了后者。
失望吧?对于皇族视百姓为粪土的举动,在民能载舟,亦能覆舟的教育里,他选择用人生最后一阶段,保国土完整,任内部怎么分裂,肉要烂就得烂在一个锅里一样,绝不允许别人往里伸筷子,这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后一举了。
凌湙的分析里,已经帮他预见了未来皇朝的走向,从江州财税归不进户部财报开始,或早或晚那边都得出事,若有压得住的太子即位还好,可惜从上到下扒拉,没有可令朝野赞誉的继承人出现。
也有,闵仁太子,只是过早的被他们扼杀了,而掌控在手里的那个,时间上并来不及他成长,若无凌湙横插一杠子,或者他也能被赶鸭子上架,可惜没有如果。
从换子的那一刻开始,命运的齿轮就偏了道,成龙的入了沟渠,让潜伏在暗河里的食人鲨,一口咬掉了角。
龙丢了角成蛟,鲨上了岸则是要称霸一方的。
武大帅突然就乐了,眼神湛湛的望着凌湙,“当年宁公盘据北境,满朝官宦都怕他举旗谋反,又是宣他妻儿进京,又是封他后人为妃,一步步蚕食他在北境的威信,直至他到了致仕之龄,才算放回了一半心进肚子,又用了许多年,才让北境改姓,却不料兜兜转转,我也走到了当年宁公的处境里,呵,如今想想,宁公从未有反心,却叫猜忌寒了心,他老人家豁达,上交兵权,移居京畿,从此未再过问北境事务,做到了兵解的极致,而我……不如他老人家多矣!”
凌湙抬眼与其对视,却未接口,武大帅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,继续道,“宁氏从一等公府没落成三等侯爵,连先太后都默认了衰没,没有阻止今上的打压,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家降等失爵,归于平民之身,便是我,早前也未觉得陛下行为有偏差……”
似是说的口干,武大帅端了凌湙为他倒的茶抿了一口,“现在想想,这与过河拆桥之行有何异?又与猜测堤防我有何异?都做的是无情无义之举,先太后可能就是看透了陛下的本性,才没有替侯府求情,反而以此保了宁氏最后的底蕴,没叫陛下和朝官一举查抄了宁氏,也让你家得以苟延残喘到了今朝,最终等得了你这样的麒麟子,呵呵,这是不是轮回报应?”
该你宁家的江山,终归是要还的。
武大帅磨搓着手中杯盏,咽下了最后一句话。
当今先祖与宁公兵伐天下时,论整体兵将实力,是不及宁公的,只不过后来二人的走向分了上下,概因了性格决定命运,前者目标只有一个,就是兵指前朝京畿,不计代价抢登为皇,后者却又在中间考虑到了领土完整,是失北境五州之地成就自己的霸业,还是救百姓于水火保证国民安定。
在有外敌入侵的当口,在成王败寇的抉择里,后者坚定的选择了驱外敌而保国民,当年年轻气盛,读那一段史时,总觉得宁公的选择过于妇人之心,国土有失可以追回,称王称霸的时机一旦错过,可就没了,换谁来都不会指责当今的开国先祖行事有差,可当自己也站在北境的这片土地上,看着生活在这里的平民百姓,便是假设有外敌进犯,肆虐国民,那一股锥心之痛就不能忍受,于是,再去看宁公当年的选择,便也不难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。
人是活的,高位却是固定死的,他能举兵反前朝,也能举兵反今上,而叫他就此罢手的唯一原由,便是开国高祖后来的一系列治国方针,没有空口大话的辜负百姓,做到了世态安稳,给百姓一口休生养息之地,或许,这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