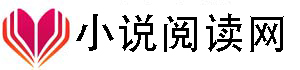40-50(14/26)
夜色里,看不真切。衔池望向他的那刻, 才忽觉夜色沉寂。
风从他那儿吹过来, 寂寂无声,她没来由地心脏一紧, 似乎某一刻极短暂地与他感同身受。
是陈年旧疾,早不似新伤一般狰狞, 疼也隐到了暗处去。可伤还是伤,时间过去,茧覆上一层又一层, 也还是疼。
宁珣踩过几片枯叶朝她走过来, 响声窸窣。
乍一看他与平日没什么分别。无论前世还是今生,他这一日,都是该上朝上朝,该用膳用膳,她曾打听过,他正常得很。
不过是因着心情不好,原本的“仁厚”褪下去, 显出杀伐果决的那一面, 瞧着便易怒一些, 人也分外冷一些。
所以上辈子每逢这一日,她都很识相地不去他眼前乱晃。
宁珣朝她伸出手,她搭上去,被他拉起来。
她起身站稳,他便松了手,不像先前那般顺理成章地牵着。
他看了蝉衣一眼,视线又回到衔池身上:“八年前的事儿,她才多大,能知道什么?为何不问孤?”
衔池抿了抿嘴,“不想惹殿下伤心。”
蝉衣知道这时候自己应该退下去了,但见太子身边没带宫人,也没提灯,便将放在一旁的灯盏递给衔池,却被她推回来。
她摆了摆手,示意蝉衣先走。
宁珣身边多少伺候的,不会连盏灯都没备好,他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里,便说明他不需要。
况且她这盏灯本就是给蝉衣带的——小姑娘眼睛都哭肿了,夜里容易视物不清。
蝉衣走远后,最后一点光亮也隐没。
她随着宁珣往前走,也不问去哪儿,一时只听见秋虫嘶鸣,和衣袖擦过的簌簌声响。
今夜月色暗沉,她看不太清脚下的路,不觉便离宁珣近了些,紧挨着他走。
眼睛看不清,其余感官便被放大,譬如她不小心碰到他手的触感。不同于她四季冰凉的手脚,他身上温度依然偏高,入秋后这温度便显得舒服了,让她情不自禁想靠近。
周遭漆黑一片,多少会叫人不安。手相碰的那一刹她下意识想握住他手,好在转瞬便克制住。
宁珣带她去了一座凉亭。
迈上石阶时,衔池少数了一级,被绊得一踉跄,他及时抓住她小臂,将她往上带了一步。
隔着衣袖,他的热量顷刻间便传过来。
又如常抽离。
凉亭正中有一张石桌,石桌左右各一只凳子,宁珣先坐了,抬眼看她:“坐吧。”
石桌上摆了酒,他顺手给她也斟了一杯。
东西是早备好的,除了酒,还有一把长剑横在桌上。衔池行过谢礼接了酒盏,好奇地打量了一眼那把剑,“殿下常来这儿?”
“一年一回。”他将那把剑拿起,见衔池好奇,便握住剑鞘,将剑柄朝向她,“试试?”
她学过剑舞,可用的多是又薄又轻的软剑,他这把剑长且重,衔池两手握住剑柄才抽出来。
铮然一声,寒光冷冽。
虽不懂这些,但她也看得出,手中的是把神兵。
衔池伸手想碰碰剑身,指尖不过刚探过去,便被他眼疾手快一把攥住:“很利,小心。”
她指尖在他掌心挠了挠,被他倏地攥紧,停留一霎,又缓缓松开。
“这把剑陪孤在边疆待过四年。”
衔池“啊”了一声,后知后觉这把剑下斩过多少亡魂,颈间没来由地一凉,当即没了细看的心思,将剑递还给他。
宁珣轻笑了一声,收剑入鞘,随手搁到一边儿。
杯中酒烈,一杯下肚她就有些晕乎,听见他低沉嗓音敲开她的醉意:“不是有话想问孤?”
衔池趴在石桌上,支颐看着他:“怕殿下不想说,惹殿下不高兴,不如不问。”
夜色深沉,她看不清他的神色,只听他慢慢同她道:“你来问孤,孤若是不想说自然就不说。无论何时,与其借他人之口,孤更希望你能自己来问。”
“何况你惹孤的时候难道还少?”
衔池抿了一小口酒,从善如流问他: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