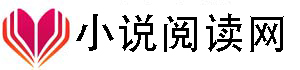90-100(8/25)
将军出兵云丰。”“起来。我在北疆待了这么多年,这些虚礼,早就不讲究了。”宋轩眼也没抬,发觉她没有要起身的意思, 手中火钳朝外头一指, 这才看了她一眼:“就是跪我也没用。那里头有间佛堂, 你若闲得慌,不如替你家殿下去拜拜佛。”
话说完,他“当啷”一声扔下火钳起身,“夜里要下大雪,这屋里暖和,留给你睡了。”
见他要走,衔池猛地提高了声量:“即便不为太子的安危考虑,将军可有想过云丰城内那两万守军?”
宋轩脚步一顿。
“胡总兵是圣人亲调来北疆的,满打满算不过一年,云丰城里头,有不少将士昔年也在宋字旗下罢?”
“将军究竟要如何才肯出兵?”
宋轩转过身,对上她那双执拗眼睛时,竟笑了两声,指了指她身后不远处的兵器架子:“我那把重剑,饮血多年,上回来了个云游的僧人,说是剑上煞气太重,得在佛前敬奉三天三夜,消消业障。”
“若是业障消了,我便顺姑娘的意,也当结个善缘。”
那把剑沉重,寻常女子连单手拿起来都困难,遑论还要在佛前跪奉三日,天又这么冷——他是在找由头,让她自己退缩。
衔池依言看向兵器架子,去将那把重剑取了下来,连着剑鞘一同双手奉着。
这剑随宋轩征战多年,是把真正的凶刃,手上没沾过血腥的,任是谁见了心底都得抖上三抖,她也不能免俗。
本就有些怯,她又对兵刃的重量没数,刚取下来那刻不免被压得一踉跄。
宋轩好整以暇地等着她的反应,见她垂眸似是在掂这把剑的重量,及时递了句话:“若觉得难为,便罢了。太子在云丰不会出事,安排你过来,本也就是让你安心在这儿等着。”
衔池却倏地攥紧了那把重剑,抬眼直视着他:“将军言而有信。”
如此油盐不进,宋轩也没再多说什么,挥挥手走出去:“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”
当夜他便听人禀告,说那丫头片子在他走后,直接去了佛堂跪着——虽说也没人看着她,但她也两手奉着剑跪得板正。
天寒地冻的,宋轩叫人将本来屋里那三个炭盆全给她搬去了佛堂,便再没过问。
只要人别死在兴广,其他的,倒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青衡也是这么想。
他只是奉殿下之命负责宋衔池的安全,至于她过得舒不舒坦,跟他何干?
衔池稍稍活动了一下胳膊——这剑太沉,坠得厉害,这才一个时辰手臂便酸得不行。
佛堂不比屋里,四面漏风,炭盆即便堆在她身边儿烧着,也暖和不到哪儿去。
蒲团太薄,泛着凉气,她将自己的大氅偷偷在膝盖下头垫了垫,仰头去看供着的那尊佛像。
佛前的香炉里有沉灰,应当是前些日子敬过香,但佛像上却蒙了一层厚尘。
从军之人,出战前讲究讨个彩头——兴许也真的有人以此为寄托,有个信仰,好叫自己在沙场上更无畏些。但宋轩显然不是此类。
她跪了一夜,几乎冻僵过去,天亮后有人来给她送饭,热乎的米粥,她囫囵喝下去才觉活过来一些。
再到日暮的时候,剑已经举不高了,稍抬高一些,胳膊便抖得厉害。
又过了一夜。
好在宋轩第二日来了。
宋轩本没打算再过问她——三天,她要是撑不过去晕了,自然不会再闹,叫军医来给她看看,保住命就是。要是真能撑过去也无妨,打晕了也是一样。
他之所以还过来这趟,是因为无意间听他的副将刘北提了一句,“倘若将军的雁雁还在,今年约莫也就是宋姑娘那般年岁,又巧在同姓,说不准会有些相像。”
怪不得他第一眼看见这丫头片子的时候,就觉多少有些亲切——也不全是这丫头知礼数的缘故。
宋轩恍惚了一霎,才回过神来笑着同刘北道:“胡说,雁雁要是还在,铁定不会跟这个似的这么拗。”
如果雁雁还活着,原来也出落成大姑娘了